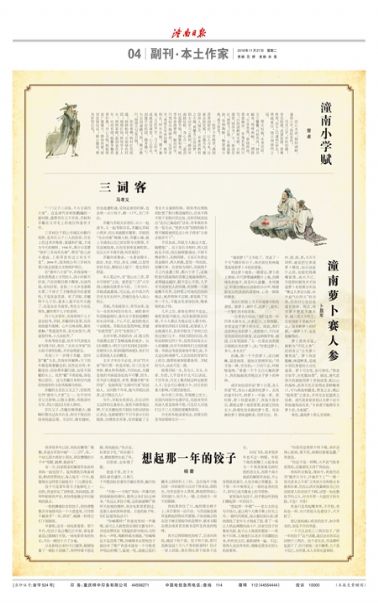
第A4版:要闻
杨莙
很多很多年以前,我妈在糖果厂做糖,我爸在军营中喊“一二三四”,我,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,则在懵懂的日子中“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”。
有一天,回家探亲的解放军叔叔和我妈一起包饺子。盐肉漂洗后准备剁馅,鲜肉凭票供应,每人每月一斤半,能像现在这样想买就能买?门儿都没有。
饺子可是看年看月才能够吃上一回的,我爸卯足了劲和面,我妈剁馅,那呯呯嘭嘭的声音,欢快得就像过年时敲响的鼓点。
一枚枚腆着肚皮的饺子,很快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大瓷盘里,只待那个解放军“一双,两双”,喊操一样将它们下到锅里。
早着呢,还有一场电影要看。那个年代,吃饺子是让嘴巴打牙祭,看电影就是让眼睛打牙祭,一场电影带来的快乐,不比一顿饺子少了分毫。
从电影院出来时天已擦黑,眼睛饱餐了一顿肚子却饿了,我哼哼着不想走路,我妈就说:“快点走,好煮饺子吃。”我吞着口水,脚底骤然生起了风。
回到家,全体傻了眼。
瓷盘子里,饺子大部队离奇遁形,只剩几个开膛剖肚的重伤员躺在那里,触目惊心。
“天啦——天呢!”我妈一声凄厉的抑扬顿挫的啸叫,骤然让我们回过神来。“我这么多饺子哦,这些耗瘟啊!”那呼天抢地的模样,我在电影里看到过,是要人命的那种表情。万恶的耗子呀,你们还要我妈活不?
“你喊哪样?”我爸突然间一声暴喝,或可让人联想到京剧《甘露寺》中,乔国老赞叹张飞勇猛的那句唱词:当阳桥头一声吼,喝断桥梁水倒流。“你喊嗬还不是没得了啊,你喊嗬未必那些饺子就回来了嗦!”我爸本就有一个可练美声唱法的嗓门,猛地一吼,或能让鼠们藏身之洞府抖上三抖。这位每年才能回家一次的彪形大汉对于我来说,很陌生,当然也很令人畏惧,瞧他那两扇心灵的窗口,虽不大,一瞪,立刻成为一双牛的眼睛。
我妈果然住了口,她仰靠在椅子上,双目紧闭一动不动。与其说她是被我爸掀起的阵仗所震慑,不如说她正陷在饺子被无情掠夺的悲愤中,根本无暇去理会或者甚至根本没听见我爸的咆哮。
我不记得那晚吃的啥了,后来问我妈,她说下的干面。饺子和干面,那可是路迢迢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呀!估计一家人的脸,准拉得比那干面条子还
长。
时间飞快,很多很多年也不过一转眼。年轻干练的制糖工人摇身成为一个周身皆被毛病叨扰的老太太,而那个高大威武的解放军叔叔,不止变得慈眉善目,头发亦被白雪覆盖。至于那一年中难得见上一面的金贵的饺子,则早已成为餐桌上的寻常物。
家里每次包饺子,似乎都会听到他们聊起那一年的饺子。
“想起那一年哦”——老太太的这句开场白,遂让两个人携手乘上时光之舟,一路叽叽呱呱,指点着回到从前:腊肉漂洗了老半天才剁成了馅、看了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片、回家后饺子的集体失踪、耗子让人绝望的嚣张……那些个旧事,又被他们从老岁月里翻捡出来,吹吹灰尘后,重新演绎一遍。不过,看两人说说笑笑的,倒像是置身在别人的故事里。
“你看你急得那个样子哦,幸好没得心脏病,要不然,病都怕要着急翻。”我爸说。
“你还不是一样啊,大声武气脸青面黑的,活像要吃人样!”我妈说。
我妈所言极是,现如今,我爸仍在用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之类的古诗和格言来教育孙辈,仍在以消灭残羹剩饭为己任而致家人的劝说于不顾,试想一如此勤俭节约之人,对当年那一大盘饺子的失踪,不急?才怪!
我爸只是弯起嘴角笑,不开腔,我妈也一样,亦只管低头包着饺子,不开腔了。
曾让爸妈痛心疾首的饺子,如今带来的,却是不尽的笑意。
一个月总会吃上三两次饺子,“那一年的饺子”这个话题,就总会在我耳边回响个三两次。说个老实话,耳朵都听起茧子了,但只要他二老不嫌累,几个茧子而已,无所谓,本人非常乐意奉陪。



